作者马建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培育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或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和克服国家危机,国家领袖和民族精英此时需要培养强大的国家认同,培育公民的国家身份意识,以推动国民为民族国家的“大我”利益而付出“小我”的牺牲。如罗伯塔·科尔斯所言,“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言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包括那些没有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界定国家特性和合法化国家存在的手段,并因此发明或复兴一种集体身份”。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一战曾令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认同发生深刻的改变:一战令美国的国家身份从19世纪的自由典范转换成世界领袖;一战也令日本的国家身份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成东亚帝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家身份变革影响了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使得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战的爆发,令深陷欧洲战场的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视此为实现“东亚帝国”梦想的天赐良机,遂在1915年1月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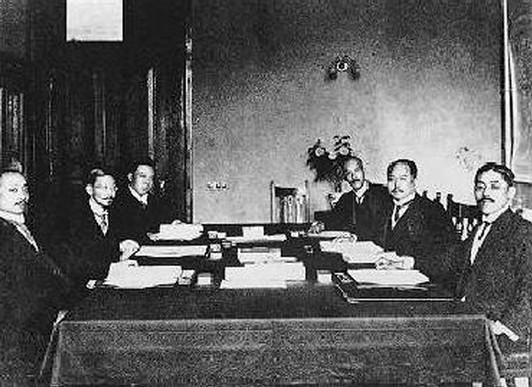
图源于网络
“二十一条”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围绕“国耻”而产生的爱国主义话语成为一种主导性话语,引导着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自我理解。日本的敌国身份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认同:一是强化了中国的民族同一性,促使中国人反思作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者?二是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到中国虽是一战的战胜国,却仍属于任人宰割的弱国。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虽然“二十一条”不是中国人遭受的第一个国耻事件,但其在近代中国人历史记忆中的重要性却是其他国耻事件不能比拟的。由于“二十一条”的存在,中国第一次有了法定的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内容编入学校教科书,把教育对于国家主义启蒙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耻记忆是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其目标在于培养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是一次国家主义的精神启蒙。本文试图探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在一战时期的形成与演变,考察国耻记忆如何培育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一、“二十一条”成为国耻记忆
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原本是一次绝密的、非常规的外交事件。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二十一条”要成为公共性的国家耻辱,首先必须被泄密。袁世凯起初对于“二十一条”是否应该泄密持犹豫态度,但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鼓励下,将“二十一条”内容以及谈判过程及时透露给国内外媒体。中国报界针对“二十一条”交涉的系列报道是培养公众关于“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最早的宣传资料。在交涉期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日期5月7日和中国对日本通牒的覆文日期5月9日,随后成为象征“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两个重要日期。
最早意识到“二十一条”交涉具有特别的“存史价值”的北京政府官员,首推外交部参事顾维钧。顾氏认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默然接受提出有损国家主权要求的最后通牒,这是很不寻常的。必须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5月13日,陆征祥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全文发表了顾维钧起草的声明,向中外宣告了中日交涉始末。北京政府此举,既是向后世有所交代,也是为了向民众灌输国家主义观念。为此,北京政府顺应舆情需求,制订了国耻纪念日,将国耻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计划。5月14日,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全体代表,称:“交涉蒙耻过去,国民教育方亟,请各代表通告各本省大中小各校员,唤起国民自觉,为救亡图存准备,愿大家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教育部下属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于5月21日复电江苏省教育会及穆藕初称:“本会已议决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通令各级学校,“以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以为鞭策国民之一法”。此后,5月9日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国耻纪念日”。
5月12日,教育总长汤化龙在全国各省教育会第一次联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今后要注重道德教育,使学生“急公好义,爱国忘家,乐善好输,培国本于现在;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教育部决定,“将此次中日交涉情形编入各种教科书,俾国民毋忘国耻”。5月底,袁世凯密谕京内外各省长官,督促他们效法日本强盛之道,“普及教育、明耻教战”。旋即,教育部于6月初向各省发出关于精神教育的咨文,其中说道,“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普败于法,乃以其事日诏国人,厥后战胜。论者咸归功于国民教育”。为贯彻教育部的咨文,6月20日,江苏省校长会议做出决定,要使用一切教育手段,“务使人人知有此辱也”。
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也遵照教育部的咨文精神,及时推出了各种新版教科书。1915年7月初,中华书局发行一整套“新制小学教科书”,其宗旨是“能令学子奋发自强,不忘国耻”。此外中华书局发行的“新制单级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也是“注重国耻,多采经训”。同时,中华书局还推出“新编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旨在激发学生的道德心、责任心、雪耻心和爱国心。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师范教科书”,其特点之一,即在于各书材料“皆取最新学说,注重国耻,而于先民之道德,固有之国粹,尤为注意”。
总的看来,教育部和出版界在培育公众关于“二十一条”的国耻记忆的态度上是积极主动的。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二十一条”可以成为引导公众舆论、抵制日本外交压力的“特殊武器”,也意识到如果对“二十一条”加以有效的宣传利用,就可以强化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而产生维护政府统治的效果。在中日交涉期间,中国政府虽然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发出取缔反日运动的命令,其实不过是敷衍日本的一种外交策略。当中日交涉结束之后,民众运动已经对政府外交失去后盾的作用,袁世凯政府才下决心彻底取缔反日运动。5月26日和6月29日,袁世凯两次发布总统令,严禁排日运动的发生。
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全权委员签署《民四条约》,由此结束了约4个月的“二十一条”交涉。在舆论压力下,负责签约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不得不通电“自请罢职”。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利用“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进行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动员。早在4月22日,中华革命党就从日本向国内、新加坡、旧金山等地散发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通告,指责袁世凯“宁肯举祖国之河山,移赠他族”,攻击袁世凯“为卖国之罪魁”,呼吁“讨贼不容缓”。很快,北京政府就意识到中华革命党人对其国耻记忆控制权构成威胁,北京政事堂在5月24日致电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指示“报纸造谣,党人煽乱,亟应查禁”。次日,袁世凯又下令究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通令称:“逆首孙文近乘中日交涉和约成立之后,在日开会密议,诋毁政府甘心卖国,藉词伐罪吊民,密派党徒,潜赴内地”,饬令各地严加防范。
为了消除革命派关于“二十一条”的负面宣传,北京政府试图控制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解释权。5月26日,袁世凯颁布总统令,指出:“凡我国人正宜求其在我勉为万众一心,冀有转弱为强之一日。讵可徒逞气血,孤注轻掷,自蹈危亡之惨祸。除饬令各道县将交涉前后情形,详加比较,向商民各界切实宣布,以释群疑外,用特明白谕示。”为了防止革命党人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转化为革命动员的政治手段,1915年6月19日北京政府出台《惩办卖国贼条例》,其中对卖国贼的定义是:“本国人民勾结外国人为卖国之行为者为国贼,治以卖国罪。卖国罪由大理院或军政执法机关审判之。”关于“卖国罪”的构成,条例给出三个标准:“一、勾结外国人意图扰乱本国国家之治安及人民之公共安宁秩序者;二、私与外国人订立契约损害本国国家及人民之权利者;三、其他勾结外国人为不利本国国家之一切行为者。”这一条例应是针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因为北京政府获悉孙曾向日本许诺,“日本可以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同时,北京政府还发布命令,劝说民众不要被“奸党”谣言迷惑:“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诪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欲乘国民之愤慨,藉簧鼓以开衅端,其居心至为险狠。”
简言之,“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培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革命党人,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二十一条”作为一种国耻记忆,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尽管《民四条约》是在日本的威逼之下签署的,但北京政府也难逃“御国无能”的干系。一个值得注意的舆情变化是,自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要求之后,“人心始去”。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据此认为“二十一条”交涉历史就是袁世凯“甘心卖国”的历史;换言之,孙中山是在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作为革命动员的宣传依据。如果说北京政府与革命党人对“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的关注更多基于政治竞争的考虑,而一般社会各界对国耻记忆的关注则更多担心国人的遗忘,他们对国耻记忆的塑造也是为了克服人们对这段国耻的遗忘。





